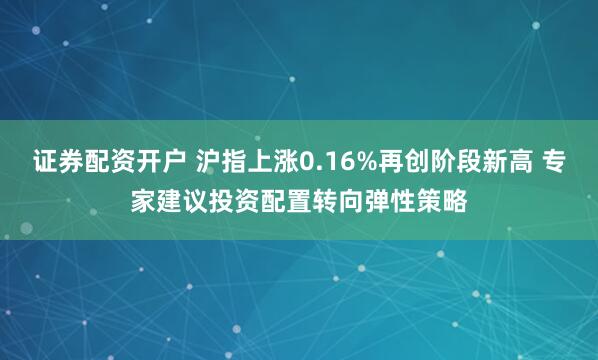《西游记》的作者吴承恩是淮安人,他的故居在河下古镇的打铜巷尾证券配资开户,到1980年当时的淮安县委决定重修吴承恩故居时,那一片废墟还依稀可见。

把那片废墟确定为吴承恩故居,依据是一部从图书馆翻出来的地方史志著录《山阳河下园亭记补编》。
《山阳河下园亭记补编》成书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,作者名汪继先,河下镇人,系清代榜眼、道光上书房师傅汪廷珍后裔。汪家世代官宦,到汪继先虽然已无功名可言,但以行医为生,仍在缙绅乡耆之列;汪继先以他所知,在前人的《山阳河下园亭记》基础上编订了一部《补编》,是上世纪中期河下古镇的实录,当时的河下尚未十分破败,历史遗迹甚多,所以《补编》的可信度甚高,留下的资料十分珍贵。
其“射阳簃”条下云:

前明岁贡生吴公承恩著书室也,在打铜巷尾。额为沈十洲殿元坤所书,书法褚、欧,笔力刚劲,有锋。岁贡讳承恩,字汝忠,号射阳山人,工书。嘉靖中岁贡官长兴县丞。敏慧淹雅,复善谐剧,为有明一代淮郡诗文之冠。一时金石之文,多出其手,张文潜以下一人。所著《西游记》小说,犹为脍炙人口。……庚寅夏,同里王觐卿世伯,由泰兴归里,暇至小斋闲叙,云有藏本,因得借閲一观。
……先生著述甚富,有《射阳存稿》,又《续稿》、《禹鼎志》及《花草新编》、《射阳山人曲存》等,盖存什一云。其裔孙作梅茂才,光绪甲辰嵗试,入山阳县学。门阀清华,为吾淮世族。明清两代,凡十余世为茂才,掇巍科,登华膴,领封圻者,代有传人。著作如林,藏书亦富。后因就舘江南,全家南迁,打铜巷之宅,旋售于他姓。沈殿元所书匾额,尚存于宅中云。
其中最重要的信息就是提到吴承恩书屋射阳簃位于“打铜巷尾”,这是一个非常精确的定位,打铜巷距汪家也就百米左右,因此不会有错。

为了证实,汪继先又引用了一位更年长的近邻前辈的记录,即“同里王丈觐卿《景潜庵随笔》”中的一则:
光绪甲辰,唐案试,予获与吴君作梅同芹谱。同案公宴时,一见甚惊异,乃定交于数十人之中,因得互拜其父母。瞻其厅事,有沈十洲祭酒坤所书‘射阳簃’匾额,书法褚、欧,笔力刚健,有笔锋。款署‘十洲’二字,下有图章两方,上:‘沈坤之印’,下:‘十洲’。所惜未署年月,不知为何年所书云。
初犹谓作梅赁屋居住,亦不明何以额曰射阳簃。细询其尊人,云系其令先德承恩先生,由长兴县丞解任后,归里所居之室也。十洲祭酒所书之额尚存。
吴氏自明季以来,数百年所居之宅,未尝易主,今始知固其世守之家室也。又出其令先德手书所著《禹鼎志》原底本见示,为其家藏秘籍,而外间所罕见孤本。
又家藏其先世未刊稿本,及吾淮人著作诗文集甚多。因得陆续假钞,缘此获睹乡先哲遗著及遗闻轶事,得益良多。
作梅工书画,尤工于指头画。精篆刻,善诗古文词。家学渊源,我辈中咸推为畏友云。(《山阳河下园亭记(续编)(补编) 》,收入《淮安文献丛刻·四》,方志出版社2006年出版)
这就更使吴承恩故居确定无疑。

然而,今天提起这段著录,是因为其中另外的一个未解之谜——即尊吴承恩为“先德”的吴作梅和吴承恩的重要著作《禹鼎志》的下落——旧话重提,也是有再做一次解谜尝试的念想。
吴家有后裔吗?汪继先说有,王觐卿也说有——吴作梅;《禹鼎志》还存世吗?汪继先说曾经见过,王觐卿也说见过。但这都令人不敢相信,因为其他相关资料不支持。
吴承恩绝嗣,早已为研究者共知,其忘年交、淮安知府陈文烛说他“家无炊火”;自称“通家晚生”的吴国荣在《射阳先生存稿跋》里说他“绝世无继”;清代淮安学者吴玉搢在《山阳志遗》里说他“贫老乏嗣”,而且在所有资料里除了他姐姐一家外,没有提到有其他的亲眷旁支。
说起来,不能排除过继、收养、认同宗的可能,如稍晚一些的学生吴国荣就自认是“通家晚生”,但一般人家同族认亲的通常也就五服,所谓十辈、二十辈还能传承的,绝对非世家缨族不可,现在居然说在三百年后(从明嘉靖中期至上世纪中期),还有居于吴家老宅、奉吴承恩为“先德”的后裔,“吴氏自明季以来,数百年所居之宅,未尝易主,今始知固其世守之家室也”,岂不令人诧异?
吴承恩有一部文言志怪小说《禹鼎志》,通说已经失传,只见到吴承恩本人有一篇《禹鼎志序》保存在《射阳先生存稿》中。根据序言和相关研究可以认为,这部文言志怪应该是以大禹治水铸鼎的神话传说为基点,有数十篇的内容,大约完成于吴承恩中年。
全文:

余幼年即好奇闻。在童子社学时,每偷市野言稗史,惧为父师诃夺,私求隐处读之。比长,好益甚,闻益奇。迨于既壮,旁求曲致,几贮满胸中矣。尝爱唐人如牛奇章、段柯古辈所着传记,善模写物情,每欲作一书对之,懒未暇也。转懒转忘,胸中之贮者消尽,独此十数事,磊块尚存。日与懒战,幸而胜焉,于是吾书始成。因窃自笑,斯盖怪求余,非余求怪也。彼老洪竭泽而渔,积为工课,亦奚取奇情哉?虽然吾书名为志怪,盖不专明鬼,时纪人间变异,亦微有鉴戒寓焉。昔禹受贡金,写形魑魅,欲使民违弗若。读兹编者,傥戄然易虑,庶几哉有夏氏之遗乎?国史非余敢议,野史氏其何让焉。作禹鼎志。(《吴承恩集笺校·射阳先生存稿存稿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14年出版)
这篇序言对于了解吴承恩的生平和社会意识、文学观念的重要性显而易见,所以几乎所有研究吴承恩的篇章都会提到,当然也就愈加感到《禹鼎志》佚失的可惜。现在汪继先和王觐卿数十年前(上世纪中期)却活灵活现地说见到过此书,岂不令人惊讶?
回忆上述《补编》发现后,也有一些研究者试图循迹找寻吴作梅和《禹鼎志》的下落,但均无突破。

笔者曾发现扬州盐运衙门有一位官员吴作梅,也是贡生身份,也在清末时期,似乎有点相似,甚至还寻访到这位吴作梅有后人是合肥某校的退休教师。但最终发现,仅是同名误会而已,那位吴作梅是合肥世家,传承有序,与淮安无关。
因为多方探索无果,所以这些年再也无人提起吴作梅和他家的藏书《禹鼎志》。
但笔者始终心有不甘,因为自认为汪继先的《山阳河下园亭记补编补编》、王觐卿的《景潜庵随笔》都不可能刻意作假。
第一,汪继先笔者幼童时见过,一袭长袍,须髯飘飘,极儒雅的一方名医,怎么都不能联想到在吴承恩身上作假;第二,出现“射阳簃”和“沈十洲”“禹鼎志”都是机具识别性的证据,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之前,除了鲁迅、胡适、郑振铎、赵景深等顶尖象牙塔里的学者和极小的地方文人圈子,其余不可能知道吴氏老宅和什么《禹鼎志》,更没有什么名誉功利可言,哪来的造假动机?

所以旧事重提,希望借古代小说网微信公众号一方宝地,联络江南各地的文史研究者,期待可以找到一点吴作梅的线索。
天载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